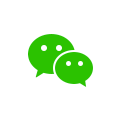有一天我会成为所有我爱的东西:空气,流水,植物,那个少年
声音的眼睛|第485-6期 点上方蓝字关注即免费订阅
路易斯�塞尔努达
塞尔努达诗十三首
汪天艾 | 译
___________
如果人能说出他爱的,
如果人能把他的爱举上天,
像光芒里的一片云;
如果就像坍塌的墙壁,
只为致敬其中矗立的真理,
他也能让自己的身体坍塌,只留下他的爱的真理,
关于他自己的真理,
不叫荣耀,财富或野心
而是爱或欲望,
我就是那个想象中的人;
那个用舌头,眼睛和双手
在人前宣告被忽视的真理的人,
他的真爱的真理。
我不认识自由只知道囚于某人的自由
那个人的名字我一听到就颤抖;
那个人让我忘记这卑微的存在,
让我的白天黑夜都随他所愿,
我的身体灵魂漂在他的身体灵魂里,
就像浮木任由海浪吞没托起
自由地,爱的自由,
唯一激我兴奋的自由,
唯一我为之死的自由。
你证明我的存在:
如果我不认识你,我没活过;
如果至死不认识你,
我没死,
因为我没活过。
我来说你们怎样出生,被禁止的欢愉,
像欲望出生在恐惧的高塔,
威胁的粗棒,褪色的生铁,
夜晚在拳头的暴力下石化,
所有面前,哪怕最反叛的,
我只适应没有围墙的生命。
铠甲穿不透,无论长矛还是匕首,
假如身体变形,一切都好;
你的欲望是吮吸这些挑动情欲的叶片
或是睡在爱抚的水中。
没关系;
你的灵魂已被宣为不洁。
纯洁不重要,命运用不朽的双手
把这天资举高到翅膀;
青春不重要,我梦想不止为人,
那么高贵的微笑,暴风雨里绸缎的海滩
来自一个堕落的统治。
被禁止的欢愉,尘世的星球,
大理石的器官有夏天的滋味,
被大海抛弃的海绵挤出液体,
铁质的花,发出回声像男人的胸膛。
高扬的孤独,低落的王冠,
值得铭记的自由,青春的斗篷;
谁嘲笑这果实,舌头上愚昧,
像国王一样卑鄙,像国王的影子
拖拽着地上的双脚
为了获取生命的一个片段。
我不知道预设的界限,
金属或者纸质的界限,
既然命运已经让他在至高的光里睁开眼睛,
那是空洞的现实、难以忍受的法条,
废墟里的老鼠都到不了的地方。
那么伸长手就找到被禁止的山峰,
被拒绝的无法穿越的森林,
带来反叛少年人的海。
但是假如愤怒,侮辱,羞辱和死亡,
这一颗颗还没有肉的贪婪牙齿,
张开洪流威胁,
你们从另一边,被禁止的欢愉,
骄傲的青铜,没有什么可以分离的亵渎,
你们在一只手上涂满神秘。
那滋味没有任何苦涩可以冲淡,
天空,闪着电的天空摧毁。
底下,无名的群雕,
影子的影子,苦痛,迷雾里的戒律;
那些欢愉的一星火花照亮复仇的时刻。
它的光彩能毁灭你们的世界。
精致的生灵:
我不希望我的声音
搅扰那树林
金黄的魅力,
你天生的元素,
沿着深色的树干
支撑着直到天际。
我愿,在这
半透明的黄昏,
浓密的一串,
勾勒你的脚印或身影,
枝条,树叶都跳动,
你和怀疑的风。
弥漫的香气,慵懒地
伴着梦的灰色脚步,
你迷失在
池塘呼出的迷雾,
那是一位恋爱中的神
动人的思绪。
你激起全部的空气,
你的魔法之下,
人的欲望,像一朵花,
那么自由地,绽放。
至高的安息
舒缓生命。
总是不确定,某片嘴唇
那样的回音,远远地,
北方白色的
桤木和桤木之间,
你瘦削的音乐震颤
在火焰里呼吸。
难道是爱,沉沉压在
你不可见的身体?
难道它对世界开的
黑暗玩笑,让你,
永生的热望,想起
蜉蝣于世的我们?
笑吧,对我说话吧,唱吧,
如果你是那股冲动
卷起燃烧的树叶,
如果那是你花冠的结局,
不竭的热情
要在死亡里实现自己。
你也会死吗?像凡间的美,
像树林狡猾的孩子
那样死吗?
你在青苔上安静,
在那片云里不说话,
某一片云雕刻,
轻盈珍珠贝的虹,
你对时日的厌倦。
我却相信看见了你的眼睛,
你平静的狡黠,
在光秃的枝头后面,
透过空气,深沉
且已冰凉,夜晚
帝王一样升起。
那是去年春天,
将近一年以前,
在伦敦,一座古老教堂的中厅,
有古旧的家具。窗户开向,
老房子背后,更远处,
草地间河水灰色的闪光。
一切都是灰色,一切都很疲倦
好像生病珍珠的虹膜。
年老的绅士,年老的贵妇,
戴着落满灰尘的羽毛帽;
窃窃私语的声音远远在角落,
摆着黄色郁金香的桌旁,
全家福和空茶壶。
落下的阴影
带着猫的气味,
在厨房惊起一阵嘈杂。
一个沉默的男人
在我身边。我看见
他狭长的侧影,几次
从茶杯边缘心不在焉地探出来,
带着同样的疲倦,
好像一个死人
从坟墓回到尘世的舞会。
谁的双唇间,
就在那边的角落,
老人们窃窃私语的地方,
稠密如落下的一滴泪,
忽然吐出一个单词:西班牙。
一种无名的疲倦
在我的脑海回旋。
灯亮了。我们离开。
几乎摸黑走过长长的楼梯
我来到街上,
当我转过身,在身边
又一次看到那个沉默的男人,
模糊地说着什么,
带着外国口音,
孩子的口音,老去的声音。
他跟着我走,
仿佛仅是迫于不可见的重量,
背负着他坟上的墓石,
但是随后他停下来
“西班牙?”他说,“一个名字而已。
西班牙死了。”
街巷突然一个转角。
我看着他消失在潮湿的夜色里。
高墙间打开的铁栅后面,
黑土地上没有树没有草,
午后那里的木凳上
安静地坐着几个老人。
周围是房子,附近有商店,
街头孩子玩耍,火车
从坟墓旁驶过。是块穷街区。
就像灰墙上的斑点,
窗台挂着雨水打湿的破布。
石板上刻字都已模糊
那下面是两个世纪前的死人,
没有可忘记他们的朋友,秘密的
死亡。不过等太阳醒来,
六月之前几日阳光明媚,
地底的老骨头也该感觉到点什么。
没有一片叶子没有一只鸟。只有石头。土地。
地狱是这样吗?不曾忘记的疼痛,
带着嘈杂和悲伤,漫长而无望的寒冷。
这里没有死亡
沉静的梦,生命还在
坟墓间搅扰,好像一个妓女
在静止的夜空下追着她的生意。
阴云密布的天空落下阴影,
工厂的烟雾在灰色
粉尘中安静。酒馆传来声音,
随即一列火车驶过,
拖走长长的回声好像怒气冲冲的黄铜。
这还不是审判,无名的死人。
安息吧,睡吧;睡吧,既然你们能。
大概上帝也忘了你们。
静默和孤独滋养着杂草
在废墟间暗沉强劲地长,
燕子失心疯地叫,
飞过广袤空气,大风下
草叶颤抖着模糊的纹路,
仿佛有不可见的身体蹭过。
清朗,雾气里的银色,那是
已经升起的尖利月牙儿
亲切的静谧洒向整片原野,
这不定的光线里,大理石的废墟
是音乐的、美丽的建筑,
由梦完成。
这就是人。看吧,
坟墓和柏树组成的大道,条条街巷
直通中心的大广场
朝向群山环绕的地平线:
一切都如常,连影子都是
几个世纪前的原样,只是没有人。
巨大的罗马渡水槽矗立
断裂干涸的拱顶倒在荒芜的山谷,
长着黄杨树和银莲花,
水从灯心草间滑过,
谜一样的雄辩流淌,
说着它的美胜过了死亡。
空荡的坟墓,没有骨灰的坛,
精致浮雕纪念的
死人早已沦为无名的群体死亡,
幸存的只有轻衣薄衫:
没有香水的瓶子,戒指和小首饰,
或是滑稽护身符象征硕大的性器,
时间用悲悯的蔑视目光原谅。
数百年前那些活着的双脚踩过的
一块块石头,还安静地
呆在原地,广场上的
纪念柱,见证每一场政治斗争,
还有献祭和守望过的一座座祭坛,
还有掩藏过身体欢愉的一面面墙。
唯独他们不在了。这样的安静
好像在等他们的生命回归。
然而那些人,易碎的材料制成,
时间的力量滋养,就算
适合成为可以抵挡时间的造物,
他们的大脑抱有永生的念头,
就像果实的核裹住死亡。
噢上帝。既然你造人是为了
让我们去死,为什么还要赐下
对永恒的渴望,把我们变成诗人?
能不能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世纪,
让创世初贪婪的黑暗里光的孩子,
像一口气吹散的种子坠落?
可是你根本不存在。你不过是一个名字,
用来让人胆怯让人无力,
没有你的生命就和这些
被你遗弃的美丽废墟一样:
在静谧的夜光中癫狂,
癫狂却绝美,在短暂轻柔的瞬间。
一切绝美之物都有定时,然后逝去。
像永生一样重要的是享受我们的时刻,
我不嫉妒你,上帝;请留我独自守着
我这些不会持久的凡人作品:
想在短命之物里装满永恒,
这热望,值过你的全知全能。
这就是人。学学吧,别再
追逐那些充耳不闻的永生神明,
你的祈祷滋养他们,你的遗忘摧毁他们。
你的生命,和花一样,只因生长绽放在
死神的臂弯难道美丽会少半分?
夜幕神圣而神秘地降下,
甜蜜如亲昵的手爱抚,
其他人有一天会安息在他的胸口,
而此刻的我前倾身体
平静地注视这片原野,这片废墟。
我不认识人。很多年我一直
寻找他们,又不可避免地逃离他们。
是我不理解他们?还是太理解
他们?这些明显的外形
面前,粗糙的血肉之躯,
假如某个热情的人将他们聚拢,
就会因为脆弱的弹力骤然断裂。
我却更理解传奇里的
死人。从他们那里回到活人中间,
加重的孤独为友,
像一个人从暗藏的源头走向
那里流出的没有脉搏的河。
我不理解河。用漂泊不定的急促,
从源头流向大海,繁忙的消遣里,
满是自己的重要性,生产抑或农业;
源头,那是只有大海能兑现的诺言,
万象大海,不定而永生。
一如在遥远的源头,将来
生命的一些可能形式睡在
在一个无梦的梦中,无用而无意识地,
迅速反射出诸神的想法。
而在未来某日的人群之中,
你会梦见你的梦,我不可能的朋友。
我不理解人。在我里面却有什么回答说
我会理解你,就好像我理解
动物,草叶和石头,
永远安静忠实的陪伴。
此生全是时间的问题,
那时间自己的节奏,悠长而广袤,
记不起另一种可悲的节奏
属于我们这个短暂脆弱的人类时间。
如果人类的时间和诸神的时间
是同一种,那么在我里面开启韵律的这个音符,
与你的音符融为一体,会踏上节拍,
而不是毫无回声地在沉默的听众里噤声。
只是我不在乎自己在
几乎同时代的这些身体里寂寂无名,
他们活着的方式不像我这来自疯狂
土地的身体挣扎着变成翅膀,
想触及那堵时空之墙,
它隔开了我的年代与你在的未来。
我只愿自己的怀抱能拥住另一个亲切的臂膀,
愿另一双眼睛分享我的眼睛看着的一切。
尽管你不会知道今天的我带着多少爱。
在那未来时间的白色深渊里寻找,
寻找你灵魂的影子,学着它
依照新的标准整理我的激情。
今天,当人们把我编进他们的目录
用他们的标准,在他们的时代,
一些人因其冷漠另一些人因其怪异都心生厌恶,
而在我凡人的颤抖里有死去的
追忆。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曾几何时当世界
吟唱我的母语,那是爱激发了这语言。
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努力,
只为我的字句不和我一起
安静地死去,而像回声
传递给你,像暴风雨过后
一个模糊的声音被风铭记。
你不会知道我怎样克制着自己的恐惧
让我的声音成为我的勇气,
徒劳的灾难都交付遗忘
它们轮番用愚蠢的享乐
滋生和践踏我们的生命,
那是你将拥有的生命,那是我几乎已经拥有的生命。
因为我预感到在这人类的疏远里
多少我的东西必将为后来人所有,
而这般孤独怎样终有一天熙熙攘攘,
尽管已没有我,却和你的形象全然相惜。
弃绝生命,是为以后找到它,
依着我的欲望,在你的记忆里。
天色已晚的时候,还在灯下
读书的我忽然停下来,
听雨声,如此浓烈的沉重
尿在街头冻结的昏暗里,
心里什么脆弱的东西就这样低声说:
囚禁在我身体里的那些自由元素,
它们只是为了这被召唤
到大地?还有别的吗?如果还有,去哪里
找它们?我不认识此生以外的世界,
如果没有你,有时候会很悲伤。请用怀旧的情绪爱我,
就像爱一个影子,就像我如何爱
已逝的那些名字之下诗人的真实。
未来时日,当人类从这原始的世界、
从这已倒退回混沌和惊恐的
世界中解放,命运会将
你的手带向一卷书,那里有我
被遗忘的诗行,你打开它,
我知道你会感受到我的声音触及你,
不是来自古老的字母,而是从你内心
鲜活的深处,带着将由你主宰的
无名热望。倾听我,理解我。
在灵泊之地也许我的灵魂会记起什么,
这样我的梦想和欲望在你那里
终获意义,我就活过了。
夜幕落下的时候,玻璃后面
那个孩子,出神地看
下雨。街灯里点燃的
光比照出白色的雨和黑色的风。
雨轻柔地包裹起
独自一人的房间,
而窗帘,遮在
玻璃上,像一片云,
对他悄声说着月亮的魔法。
学校渐远。现在是
休战的时候,故事书
和小画书摆在
台灯下面,夜,
梦,没有度量的时间。
他住在那温柔力量的避风港,
还没有欲望,也没有回忆,
那个孩子,无法预知
时间正在外面静候,
和人生一起,埋伏以待。
他的影子里珍珠已长成。
白天全部的炽热,堆积
成令人窒息的水汽,从大片沙地喷发。
比照着夜空如此清澈的
蓝色,像不可能滴下的水,
星辰冻结的光辉,
新月旁边骄傲的侍从,
月亮,高高在上,轻蔑地照亮
坟地中央野兽的残骸。
远处豺狼嗥叫。
没有水,树丛,灌木或草地。
盛满的光芒里月亮望向
那可悲的客迈拉,沙漠里
被侵蚀的石块。割断的翅膀,像断臂;
时间切走胸脯和爪子;
鼻子消失后的空洞和曾经
卷曲的头发,如今住着
情色的飞鸟,靠
悲伤,死亡滋养。
当月光触及
那客迈拉,仿佛激起一声呜咽,
有一声哀嚎,不是来自废墟,
而是扎根在她心里的许多世纪,永生不死
为不能死去哭泣,像人类繁衍出的形式
那样死。死是艰难的,
然而假如一切都死了,不能死,
也许更加艰难。客迈拉对月亮轻声说话
声音那样甜美连悲伤都融化。
“没有受害者也没有情人。人都去哪了?
他们已不再信我,不再信我给出的无解
谜语,就像斯芬克斯,我的敌手和姐妹。
我的谜语已经诱惑不了他们。尽管诸神都死了,
神圣的还在,变化多形。
所以活在我心里的热望没有逝去,
虽然我的外表不再,虽然我连影子都不是;
这股热望就是看着颤抖的人类
拜倒在我面前,在我无解而隐秘的诱惑面前。
“人类,像鞭下驯养的动物,
可是,多么美丽;他的力量和他的美,
哦神啊,多么迷人。人身上的愉悦;
美丽的人,他身上有多少愉悦。
许多世纪过去,自从人类逃脱我,
自从他们轻蔑地忘记我的秘密。
虽然也有少数几个来找我,
诗人们,我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一点魅力,
我的秘密几乎诱惑不了他们,而在他们身上我也看不到美。”
“瘦削或软弱,没头发,戴眼镜,
没牙齿。这就是我迟来的仆人
外貌的部分;而且,他的个性,
和外貌一样。尽管如此,如今没什么人来找我的秘密,
他们已在女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悲伤客迈拉。
这遗忘是好的,因为,在给婴儿换过尿布
或擦过鼻子,一边心里想着
某个评论家指责或颂扬的话
之后,别来找我。
“既然他们已没有力量,没那疯狂
来信我和我的秘密
他们还能信成为诗人?
比起荒地,废墟和死亡
���我宽宏赐给受害者的奖赏
最好还是去学院里坐沙发。
一旦我掌控他们的灵魂,
人类和诗人都会宁愿
残酷的蜃景而不要平庸的可靠。
“显然对我而言那是另一个时代,
那时候我快乐地,轻盈地,踏进迷宫,
在那里我曾失去很多人,也曾赐给另一些人
永世的疯狂:想象幸福,未来的梦,
爱的盼望,灿烂的环游。
不过,对明智的人,我用有力的双爪
勒死,因为一克疯狂
是生命的盐。我曾有过的力量,
现在我已没有给人类的诺言。”
月亮的倒影滑过
沙漠失聪的沙砾。
阴影里留下客迈拉,
迷人的音乐在她甜美的声音里静默。
就像回浪的大海,退潮时
留下沙滩赤裸地面对魔力,
声音的魅惑退去,留下的沙漠
更加充满敌意,沙丘失明
暗淡,没了旧时的蜃景。
阴影里沉默的,客迈拉仿佛退隐进
第一混沌洪荒的夜晚;
然而无论是神,人,还是人的作品,
一旦存在就无法自我废止:必须存在
到苦涩的最后,消散成灰。
一动不动,悲伤的,没有鼻子的客迈拉闻着
初生黎明的清凉,又一天的黎明,
死亡不会带来怜悯,
她悲伤的存在还将延续。
*译注:客迈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女怪。
你,这全无美德的世界,
我不求你更多,
只要一小块蓝,
在空气里,在我心里。
对财富和权力的
野心都给别人;
我只想和
我的光我的爱在一起。
回去?回去的是这样的人:
经过漫长年月,经过漫长旅途,
行路疲乏,渴求
他的故土,他的家,他的朋友,
还有忠实等他归来的爱人。
至于你?回去?别想归程,
而是要继续自由地前行,
年轻或老矣,随时可以上路,
不像俄底修斯,没有找你的孩子,
没有等你的伊萨卡岛也没有珀涅罗珀。
继续,继续前行,不要回头,
忠实地直到路的终点,生命的尽头,
不要挂念更容易的命运,
你脚下是从未踏上的土地,
你眼前是从未见过的风景。
飞鸟的歌唱,在黎明,
天气最温和的时候,
活着的快乐,已从梦境
溜出,用愉悦感染
向着新一天醒来的生灵。
家门口,小孩子
一个人,和自己玩,
冲着他破旧的玩具
微笑,在这快乐的
蒙昧里,享受发现自己活着。
诗人,在纸上梦着
他未完结的诗行,
他觉得很美,享受着,思考着,
用理智和疯狂
什么都不重要:他的诗存在。
提醒你也提醒其他人,
当人类的低贱令人作恶,
当人类的冷酷令人发怒:
这一个男人,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信仰。
提醒你也提醒其他人。
1961年,陌生的城市,
已是四分之一世纪
过去。背景不足提,
你被迫参加公众朗读会,
因而得以与那男人交谈:
林肯纵队的
一位老兵。
二十五年前,这个男人,
尚不认识你的土地,一切对他遥远
而陌生,他却选择去那里,
决定,若时机已到,就为那里赌上性命,
对着那时候木板上挂出的理由
他宣誓,尊严就是
为倾其一生的信仰奋斗。
那个理由也许丢失,
已不重要;
至于很多其他人,假装信仰,
却只关心自己,
更不重要。
重要的,足够的,是一个人的信仰。
所以今天那理由又一次出现在你面前,
就像那些日子里一样:
为之奋斗何其高贵而富于尊严。
他的信仰,那个信仰,他仍留存,
经过那些年,那场失败,
当所有一切都似乎背叛。
而那个信仰,你对自己说,是唯一重要的。
谢谢,战友,谢谢
你的榜样。谢谢你对我说
人是高贵的。
无论多少毫不重要:
一个,哪怕一个也足够
成为整个人类的高贵
无可辩驳的见证。
*译注:1936年是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年份。

声音的眼睛

id:shengyindeyanjing
长按二维码 直接关注